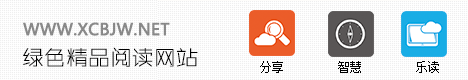关于图书馆和我,也算是一段悲欢史,该从何处说起呢——这样的开头,大有“不道别来愁几许,相逢更忍从头诉”的意味,但其实当然是恩多于怨、乐多于愁。
一
妈妈至今还记得我第一次去深圳市图书馆时我惊讶万分的样子。
那时我们已举家南迁——从湖南移居至深圳——妈妈找的新工作需要参加职业资格考试,因此她每个周末都要去图书馆复习。12岁的我跟她一起去了那里才知道,以前去过的中学图书馆是何等简陋。
阿根廷最著名的图书管理员博尔赫斯说过的最著名的话,无关镜子、迷宫和交叉小径的花园,而是这一句:“如果有天堂,大概就是图书馆的模样。”诚如是言,深圳市图书馆无疑是少年时代的我见过的真正的“天堂”。初到大都会,我忍不住给留在湖南小城的好友写信炫耀:“这里不光有无数版本的《红楼梦》,还有《红楼梦魇》和《红楼梦补》!”整整一个月后,好友才回信淡淡地说:“那你就替我们多看些书吧。”
迟钝的我这才意识到可能伤害了旧友的感情。而我已经幸或不幸地在图书馆里发现了言情小说专架,从此弃红楼于不顾,从岑凯伦、琼瑶一气看到亦舒、梁凤仪,乃至著名创作团体“雪米莉”。直到大半个暑假过去、熟谙了所有港台言情套路,我才罢休。紧接着,我又发现了金庸、古龙、苏童、陈丹燕,明清小说,还有《青鸟》和《骑鹅旅行记》,等等。
高雅和滥俗在同一个图书馆里和光同尘。也就是说,它们安然共享同一个“天堂”。刚转学到深圳的我时常逃学。原因很简单,就是迷路。
那条下车后穿过私立医院去学校的小路走过若干次了,但也许因为岔路太多,我还是很容易迷失方向——也有可能是自己潜意识里故意的——等终归正途时,往往已经迟到,而迟到就势必被罚站。每当此时,我就果断地决定逃学——反正上课也没有什么意思。也怨不得老师总罚我站。那年我刚上初二,正是惨绿少年的年纪。觉得没意思就想逃,可是深圳这么大、这么冷淡,逃到哪里去呢?我并不知道。

那天妈妈的表现着实古怪。在深圳10月依然灼人的正午骄阳下,她领着我往学校一路疾走,一言不发,吓得我肝胆欲裂。到学校时已过饭点,她便在外面的小饭馆要了两份盒饭,吃饭时还是全程板着脸一言不发。吃完差不多已到上课时间,她才说:“你快去上课,不许再逃。”
我灰溜溜地走了,一下午都在忐忑,不知回家后会受到怎样可怕的惩罚——然而,那天晚上并没有发生什么,此后的很多天,都没有。好几年之后,妈妈才告诉我,其实她那天一直在拼命忍着笑——一个逃学都逃往图书馆的小孩,能坏到哪里去?可又不能笑,一笑,就没法教育了,万一以后再逃学怎么办?
二
另一个关于图书馆的记忆,是常在图书馆里遇到骚扰者。
在图书馆的开架阅览室里看书,脖颈处偶尔感到异样灼热——猛一回头,总能看到一张慌乱潮红的脸,我便如受惊小鹿一般逃开,但还是舍不得放下手中的书。倘若来者再次逼近,我只得放下书快速逃离。有一次受惊吓太遽,我在这座尚且陌生的海滨城市的大街上狂奔,犹如奋力逃离身为一个少女的危险宿命。
而在记忆中狂奔不止的画面里,大街上的夕阳总是惨淡灰黄,公交车站则像永远也抵达不了的、足以自保的成年时光。
过了那段危险期,再在图书馆遇到搭讪者,早已练就应对之法。就读研究生时期,有一次在阅览室自习,不知为何总感觉对面有两个小火团灼热地投向我。终于,一张纸条“啪”地按在我看的书上。我眼皮都不抬,当即收拾东西起身。还没走过长廊,空荡荡的楼道里脚步声越来越近:“同学!”
我回头看那人,他比我想象中更从容:“同学,可不可以告诉我你的电话号码?”
彼时我早非惊惶如雀的13岁女孩,正色道:“同学,你不觉得在图书馆这樣影响别人学习不好吗?”
他似乎吃了一惊。
过了几年,某个冬夜又在国家图书馆遭遇搭讪者,已经不再那么可笑地大义凛然了。搭讪者同样是看我离开阅览室,一路追出,在万家灯火次第亮起的中关村大街上大喊:“你读几年级了?”
我想了想,还是平静地回头:“已经工作了。”
那个中年男人“哦”了一声,听不出失望还是别的:“你看上去很年轻。”
我忍住了没说“谢谢”。
问话熟极而流,也不知道重复了几百上千次:“请问,我有这个荣幸可以认识你吗?”
“并没有。”我同样礼貌地回答。
也许是长大后渐渐就理解了,在图书馆搭讪成年女子的人和骚扰者不同,多数还是耽于幻想的多情种子。这样一想,我多少就原谅了这些搭讪者。
习惯在图书馆里追逐女孩的男人们,在书与书的空当处茫然四顾,幻想颜如玉从天而降。是读书给他们制造的幻觉,抑或被某种孤独感驱使,能接近最大数量陌生女性的唯一可能,也就只有在这全然免费的“天堂”了。

还有一些时候,不一定要自己去图书馆,也可以委托他人去借书。
表妹家比我家到深圳要早好几年,她家里缴了择校费让她进了市重点中学,据说该校有全市数一数二的校图书馆,比我插班的普通中学的图书馆规模大得多。我有一次随她混进去借了本港版《唐伯虎诗词歌赋全集》,至今还可以将里面的词倒背如流:
牡丹含露真珠颗,美人折向庭前过。含笑问檀郎,花强妾貌强?檀郎故相恼,须道花枝好。一向发娇嗔,碎挼花打人。
据说这首《菩萨蛮》是唐代无名氏所作,也不知道怎么窜入唐寅的集子。唯一记得的就是这本书差点遭遇不测。事发于某节语文课,我刚把书拿出来看不久,语文老师突然过来轻敲桌子,让我去他办公室帮他拿一本书。我赶紧把书藏在书桌抽屉里,起身就走。回来后发现班里的气氛异样,下课后才知道,我刚起身离开教室,语文老师就把我抽屉里的书取出来向全班展示:“你们看看人家在看什么书!竖版,还是繁体……”
那是一个说不清楚到底是称职还是不称职的老师。同学都叫他老鬼。他看上去很严厉,会罚迟到的女生在操场上跑5圈。当时学校不允许女生蓄长刘海,中考前夕他会拿自己的刮胡刀剃掉女生的长刘海(几乎所有女生都为此露出难以忍受的表情)。他会在上课时把“干涸”念成“干固”,引得我这样的二愣子学生忍不住举手站起来说:老师你念错字了——端的是书生意气,挥斥方遒。而老师到底是什么反应,我却完全忘记了。
不过我一直没忘记那个细节,他从我抽屉里拿出书向大家展示,又在我回来前迅速放回——虽然并没有真的看到那一幕。就是这行为的出人意料,让我猜想他也许并不像表面上那样讨厌我。不光是因为唐寅、繁体字、竖版。也许更多的,只是人到中年的渐渐吃力,和面对年少轻狂的学生的不知所措。同时,又对这无知无畏不由得退避三舍,并感到某种怅惘。
人生忽如寄。当我开始懂得这点时,早已过去很多年,几乎到了和那个老师差不多的年纪。一生再也没有机会问这个被称为老鬼的语文老师当年到底是怎么想的——被一个13岁的女孩指出自己念错字,以及发现她上自己的课时却在看繁体字的古籍。
- 热门文章